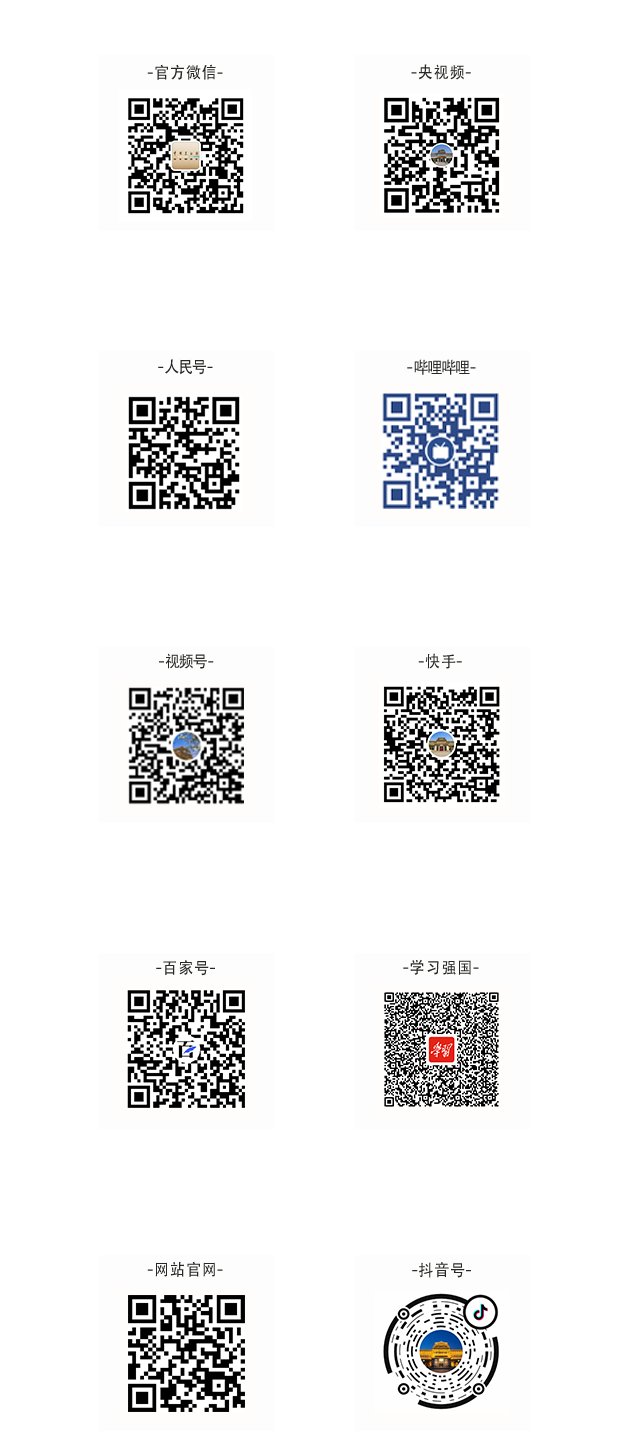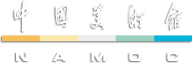有声有色 | 黄渤讲中国美术馆藏品
来源:中国美术馆
时间:2024年01月22日
 《醉卧图》表现的是一位醉饮后席地而卧的落拓文士形象。画面布局简单、稳定,除一酒瓮之外别无背景。人物大致呈横平走向,居于正中,与画面左侧的竖长题草书形成 L 形结构,平中有奇。酒瓮以极为简省的画法化实为虚,在点题“醉卧”的同时也衬托了主体。醉卧者显然年已衰暮,他以右肘为着力点斜倚酒瓮之上,垂首瞑目,颓然若有不支。面部以淡墨勾勒,淡赭烘染,幅巾则以浓墨勾勒,淡墨渲染,益显鬓发须眉的萧疏 斑白之状。值得注意的还有衣纹线条的处理。以狂草笔法入画,用之“书写”衣纹是黄慎个性化的独创,但这更多见于其占比不高的大写意作品,那种用笔迅疾多变,如兔起鹘落,每现顿挫、 提按、飞白之迹的特点,在《醉卧图》这样具有一定写实性的半 工写作品当中,通常是一种有节制的体现。这幅画中的线条手法, 融折芦、铁线和钉头鼠尾为一,特别是其笔调在顿挫方折的刚性之外,呈现出较多圆转流利的柔感,这也合乎人物的体态、姿势,甚至情绪状态。加上局部穿插枯笔浓墨以强调结构和虚实,形成整体节奏,画家对笔墨语言的理解与驾驭力可见一斑。
画幅左侧以草书题识,题语系从苏轼七绝诗《醉睡者》脱化而来:“心不能行不如醉,口不能言不如睡。先生之睡醒醉间,万古无人知其意。”不难想象,蹀躞摆荡于醒醉之间的岂独画中人而已。黄慎本人即善饮,往往醉后兴发,淋漓满纸,人以“疏狂”目之。作为“扬州画派”重要画家,黄慎对后世写意人物画产生了深远影响,但以职业画家角色立身本非黄慎初衷,好友马祖荣序其 《蛟湖诗钞》,并不讳言这一点:“慎之寄于画也,非慎志也。” 画家本人“此生足可惜,此志何能偿”(黄慎《感怀》)之类自嘲也屡不一见。如果说疏狂与抑塞的内在冲突终其一生,就《醉卧图》微窥之,似亦不诬。
林风眠是20世纪中国现代美术先驱,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重要奠基人,他是“中西融合”艺术理想的倡导者、开拓者和重要代表人物。1925年冬,不到而立之年的林风眠从法国留学归国,在蔡元培的力荐下被聘请为国立北平艺专校长,投身“改革”艺术院校的事业。他认为“绘画的本质是绘画,无所谓派别,也无所谓中西”,只有努力提倡中西艺术“调和”的主张,才能达到艺术的个人实现和精神理念的整合,从而“实现中国艺术之复兴”。
从抱定“为中国艺术界打开一条血路”的决心,到以“我入地狱”之精神主持多次西化艺术运动,其中西调和的教育理念,均未能彻底实现。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对“新画派”和以他为代表的“形式主义”的批判,林风眠离开了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开始了他在上海孤独的“退隐”生活。他不再对外宣称自己的艺术主张,按照自己的想法,在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里思考艺术。《秋鹜》即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之作。
《秋鹜》创作于1960年,与《水上》《早春暮色》《四鹭》《鱼鹰小舟》等11件作品一同收藏于中国美术馆。作品中水面辽阔,芦苇低垂,五只黑鹜高低错落,展翅低飞,优美轻快地悬于天地之间,却又始终笼罩着一层孤寂的色泽。画面通过大块水墨晕染,采花青、点赭墨,略施西法之光线结构,加以小笔勾勒皴擦,毫不费力地营造出江雾迷蒙的东方意蕴与“短暂即逝”的现代性审美。寥寥数笔,将传统绘画的气韵与西方现代绘画的形式感融会贯通。
这只毕生追求艺术理想的“孤鹜”,也在找寻绘画自身意义的苦旅中,形成了人格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独特性,走出了一条独特美的历程。
《醉卧图》表现的是一位醉饮后席地而卧的落拓文士形象。画面布局简单、稳定,除一酒瓮之外别无背景。人物大致呈横平走向,居于正中,与画面左侧的竖长题草书形成 L 形结构,平中有奇。酒瓮以极为简省的画法化实为虚,在点题“醉卧”的同时也衬托了主体。醉卧者显然年已衰暮,他以右肘为着力点斜倚酒瓮之上,垂首瞑目,颓然若有不支。面部以淡墨勾勒,淡赭烘染,幅巾则以浓墨勾勒,淡墨渲染,益显鬓发须眉的萧疏 斑白之状。值得注意的还有衣纹线条的处理。以狂草笔法入画,用之“书写”衣纹是黄慎个性化的独创,但这更多见于其占比不高的大写意作品,那种用笔迅疾多变,如兔起鹘落,每现顿挫、 提按、飞白之迹的特点,在《醉卧图》这样具有一定写实性的半 工写作品当中,通常是一种有节制的体现。这幅画中的线条手法, 融折芦、铁线和钉头鼠尾为一,特别是其笔调在顿挫方折的刚性之外,呈现出较多圆转流利的柔感,这也合乎人物的体态、姿势,甚至情绪状态。加上局部穿插枯笔浓墨以强调结构和虚实,形成整体节奏,画家对笔墨语言的理解与驾驭力可见一斑。
画幅左侧以草书题识,题语系从苏轼七绝诗《醉睡者》脱化而来:“心不能行不如醉,口不能言不如睡。先生之睡醒醉间,万古无人知其意。”不难想象,蹀躞摆荡于醒醉之间的岂独画中人而已。黄慎本人即善饮,往往醉后兴发,淋漓满纸,人以“疏狂”目之。作为“扬州画派”重要画家,黄慎对后世写意人物画产生了深远影响,但以职业画家角色立身本非黄慎初衷,好友马祖荣序其 《蛟湖诗钞》,并不讳言这一点:“慎之寄于画也,非慎志也。” 画家本人“此生足可惜,此志何能偿”(黄慎《感怀》)之类自嘲也屡不一见。如果说疏狂与抑塞的内在冲突终其一生,就《醉卧图》微窥之,似亦不诬。
林风眠是20世纪中国现代美术先驱,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重要奠基人,他是“中西融合”艺术理想的倡导者、开拓者和重要代表人物。1925年冬,不到而立之年的林风眠从法国留学归国,在蔡元培的力荐下被聘请为国立北平艺专校长,投身“改革”艺术院校的事业。他认为“绘画的本质是绘画,无所谓派别,也无所谓中西”,只有努力提倡中西艺术“调和”的主张,才能达到艺术的个人实现和精神理念的整合,从而“实现中国艺术之复兴”。
从抱定“为中国艺术界打开一条血路”的决心,到以“我入地狱”之精神主持多次西化艺术运动,其中西调和的教育理念,均未能彻底实现。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对“新画派”和以他为代表的“形式主义”的批判,林风眠离开了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开始了他在上海孤独的“退隐”生活。他不再对外宣称自己的艺术主张,按照自己的想法,在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里思考艺术。《秋鹜》即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之作。
《秋鹜》创作于1960年,与《水上》《早春暮色》《四鹭》《鱼鹰小舟》等11件作品一同收藏于中国美术馆。作品中水面辽阔,芦苇低垂,五只黑鹜高低错落,展翅低飞,优美轻快地悬于天地之间,却又始终笼罩着一层孤寂的色泽。画面通过大块水墨晕染,采花青、点赭墨,略施西法之光线结构,加以小笔勾勒皴擦,毫不费力地营造出江雾迷蒙的东方意蕴与“短暂即逝”的现代性审美。寥寥数笔,将传统绘画的气韵与西方现代绘画的形式感融会贯通。
这只毕生追求艺术理想的“孤鹜”,也在找寻绘画自身意义的苦旅中,形成了人格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独特性,走出了一条独特美的历程。
《初踏黄金路》是版画家李焕民于1963年创作的一件套色木刻作品。
20世纪50年代末西藏实施民主改革后,20万户、80万农奴和奴隶翻身做了主人。这为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题材,文学、戏曲、电影、摄影、绘画等方面的优秀作品大量涌现,《初踏黄金路》就是其中之一。
画家李焕民1950年进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干部培训班,毕业后到重庆工作,有机会深入川西藏族地区体验生活,亲眼看到藏族劳动人民民主改革前后的生活对比,为创作《初踏黄金路》积累了素材。
作品的“画眼”在于“初踏”和“黄金路”。画面构图呈S形,这条S线启自画面的右上角,向左下行进至画面1/3处折向右下,这条路突然变宽占据了底边的全部。科学分析,路的透视有悖真实。显然,画家未固守焦点透视,而是将中国传统山水画中的“平远”“中远”“高远”运用在版画创作中,艺术地夸张了这条田间小路,使之成为藏族劳动人民沐浴着党的恩泽走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的美好隐喻。这种处理方式,配合全幅统一的金黄色主调,紧扣画题中的“黄金路”。此外,画面这条呈S形的结构主线,又像飘扬的五线谱,藏族女青年与牦牛就是这条乐谱上的乐符,奏响“翻身农奴把歌唱”的高亢乐曲。
画面上由近及远安排了三位青春健美的藏族女青年。她们身着白色上衣和宽厚的藏袍,三人各自牵有一条头戴大红花的牦牛,牦牛背上荷载大捆刚刚收割的青稞,行进在八月收获季节的金色田野里。三位藏族女青年,代表广大翻身做主人的藏族劳动人民,她们嘴角挂满幸福的笑容,深情地望向远方,对社会主义新生活满怀憧憬。三位藏族女青年项间戴着鲜红的宝石饰品,与牦牛头上的大红花形成呼应,巧妙地表现出藏族劳动人民对牦牛这一基本生产资料的深厚感情。
李焕民艺术创作执着勤恳,专注于藏区题材,他形容自己的艺术道路为“一生只打一口‘井’”。他在60多年的艺术生 涯中创作出一大批表现藏族题材的优秀作品,成为用艺术记录藏区半个多世纪历史巨变的不朽史诗。
20世纪初,受西学东渐的影响,一批有志之士远赴海外学习。1928年,年仅24岁的刘开渠在蔡元培的支持下获得留法学习雕塑的机会。1933年,刘开渠完成学业回国,鲁迅对他说:“过去中国人只做菩萨,现在该是轮到做人像了。”此后,不管社会环境、生活环境、创作环境如何变化,他始终心系中国雕塑事业的发展。1963年,刘开渠任中国美术馆首任馆长。
1961年8月,刘开渠被中国美术家协会安排到中国西南考察,他先后经过昆明、滇池、石林、瑞丽、南宁、桂林等地。程丽娜后来回忆说,刘开渠借此机会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写生,回到北京后根据印象创作了不少画作。
雕塑《牦牛》的牛身采取类似于绘画中留白的抛光处理,对牛的鬃毛、尾巴及腿部的毛发以线描的形式进行勾勒,并通过石材的肌理表现出毛发的浓密感和真实感,浑然一体。值得注意的是,刘开渠在1959年《提高雕塑艺术的质量》一文中强调:“雕塑造型的基础是体积,轮廓是体积的边缘。从体积到轮廓从轮廓到体积,使作品的体形完整,生命力充沛。”可以说,雕塑《牦牛》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他这一理念的实践,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融入现代雕塑创作中来,让观者感受到画中有塑、塑中有画的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