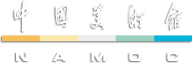融入新中国艺术思想的沃土—刘开渠艺术理论研究
在以往对刘开渠艺术的研究中,我们大都将注意力集中在他精彩的雕塑作品上,而对他留下的理论财富却认识不足。事实上,刘开渠公开发表自己对艺术及艺术批评的看法早在其专攻雕塑之先,而且终其一生,他都在不断地思考和撰著。他不倦地记录了自己各个时期的思想,仅通过其已经发表的文章,我们即可以清晰地觇见,随着对艺术的认识不断升华,他的思想发生了比较明确的几次转变与成长,由此也使我们得以划分出了可供研究的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与他的创作活动既有密切关联,又不完全重合;既忠实地反映了伴随其创作的思想变化,又体现出他在雕塑艺术以外,对更大范围内的美术现象乃至社会民生的关切和思索。这四个阶段分别是:“初涉艺术问题的阶段”“深入探讨创新问题的阶段”“主张以雕塑表现英雄与人民生活的阶段”和“倡导发展城市雕塑的阶段”。
此外,在刘开渠留法归国之后,为中国美术理论界贡献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译介文章,主要有《朴荷特尔的雕刻教学》(1934年)、《艺人伦勃朗》(1936年)、《罗丹以后的法国雕塑艺术》(1949年)、《欧洲雕刻的趋势》(1949年)、《苏联大雕刻家穆希娜的雕刻》(1954年)以及《辉煌的阿旃陀石窟艺术》(1955年)等等。刘开渠对中国传统雕塑艺术的关切和研究更是从时间跨度相当大的文章中表现出来,比较典型的代表包括《中国雕刻的过去与未来》(1947年)、《中国古代雕塑的杰出作品》(1955年)等。
一、初涉艺术问题的阶段(北京求学期间)
自1920年进入北平国立美术学校求学之始,刘开渠就十分勤奋,他不仅在绘画技巧方面下过很大的功夫,还很注意研究各类艺术问题。1924年7月24日,刘开渠在《晨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艺术上的批评》的文章,体现出他在对待艺术问题时严谨、认真的态度,文中写道:“艺术的批评,不是对于美学及艺术学没有研究的人,可以做得了的。朋友们!不欲做艺术上的批评则已,否则,请先对于美术及艺术学下一番研究的功夫,才能作出有价值的批评呢!”[1]刘开渠很注意提高自己在美学和艺术方面的修养,他对绘画、文学、历史等问题都很感兴趣,比如,他非常欣赏鲁迅、郭沫若等人的作品;受柯仲平的影响写过新诗;创作并发表过《生的折磨》《星期日》《长城上》等小说。因为兴趣广泛,他结识了郁达夫、沈从文、柯仲平、丁玲、胡也频、陈翔鹤、赵其文等文艺界人士,参与了新文学运动。在专业领域里,刘开渠组织了“心琴画会”并积极举办展览,他的艺术思想不仅从诸多此类活动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当时其发表的文章中更有充实的反映。
求学期间,刘开渠曾听过闻一多等先生的演讲,自青年时代起,就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涵养成了一种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他在1924年发表的文章《禁止展览裸体画》中便写下了这样的话:“中国人不了解裸体画,是显然的!但是怎么样才能使一般人认识、了解人体美呢?这个责任是现在的艺术家不能不负的。然而以往观察、说明人体美的文字,实在少得太可怜了。一般人之反对裸体画,固由以前的遗毒,但是现在一般研究艺术的人们不去把人体美详详细细地用文字先说明给一般人,实在也是一个大原因。所以嗣后我们不必怪一般人鄙视裸体画。我们只能说一般研究艺术的人没有尽他们说明的责任。”[2]
因为推崇陈师曾的美学思想,刘开渠非常反对墨守成规的临摹,主张到自然中去写生,追求艺术创新。在他1925年发表的《现在的国画》中有一段精彩的分析:“我以为国画的衰退有两个原因:(一)不皈依自然。自然与艺术家是不能分离的,那么不知自然是何物的近代国画家怎么会产生伟大、有价值的作品呢?没有伟大的作品出现,国画怎么能不日退一日呢!(二)固守旧法。现在的国画家哟!你们要记住:一切的规矩准绳足以破坏自然底实感,和真实的表现。你们去亲近自然,打破一切的规矩与成法,去自由自在的创造呵!”[3]话语中流露出他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关切。类似还有发表于1925年的文章《敦煌石室的壁画》,文中他再次大声疾呼中国的艺术需要在传统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古物的可贵,在能给我们以各方面的研究。我们借它不唯可以知道前代的文化如何,社会情形怎样;且它能启发我们的新的学术,新的创造,使我们的生活日趋于美善之中。如果我们不去,或不能去研究它,解释它,使它的精华应用到我们的学术上、生活上,那么就是我们周身皆古物,也是没有一点价值!所以我们对于古物要去细心地研究,阐发;只是守财奴一般地守着,实在是很没有道理的事情。”[4]
总体来说,在北京求学期间的青年刘开渠真正走进了艺术的世界,养成了学术态度与社会责任感相得兼备的艺术观,具备了既能回顾传统、又能前瞻创新的眼光和视角,为后来的不断进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是众多热情参与新文化运动的青年中的一员,为丰富那一时期中国的文艺思想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二、深入探讨创新问题的阶段(在上海、南京和杭州期间)
在北京修业7年以后,刘开渠辗转上海、南京,最终在杭州暂时安定下来。生活上的颠沛并没有阻滞他对艺术问题的思考与研究。1927年撰写的文章《评画与看画》延续了他对美术评论与创作一贯的关注态度:“画家......凭借着自己敏锐的感觉,向自然中索取美的材料,开示自然的底蕴。更用他们强大的生命力把这些美的材料,熔化、组织,另铸一种新的形体,赋予新的生命,以适合于人生的最高理想。”“批评家要给一般人一种鉴赏的方法,于是他们把研究的结果,就是作品必备的上边所说的条件定为艺术评价的标准,叫一般人依此欣赏,鉴别作品。批评家这种研究、说明、告诉一般人,叫作评画。”[5]
经过了持续的思考和积累,刘开渠在这一阶段明确厘清了临摹与创造两者各自不同的价值。发表于1927年《现代评论》的文章《翟大坤的作风》里面写道:“我们知道艺术是在于创造,创造一种新境界。使吾人在实际生活上求不到的而能不断的在艺术上得到心境的圆满。如其艺术没有创造,便失去了这种力量。失去了这种力量,便不成为艺术。传递‘宗派’,接送‘衣钵’,就像影印古版书籍,虽然能次传递其形式,不失原版面目,可是也只是能传递它的形式,不能格外予吾人以新的趣味。为保存古版书式样这样影印下去是没有什么不成的。可是以创造新境界为使命的艺术是绝对不能似此地影印下去,决不能以影印古人风派为有价值。再明白地说就是艺术不在于传递宗派,而在个人创造。如其作品失去创造的精神,而只是为前人的正传者,接送衣钵者,那不是艺术。那是影印机,那是传送的驿者。能代表一代艺术的,能在艺术史上占地位的是创作家,不是只负传送责任的驿者。”[6]
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之上,刘开渠不断地撰文阐发艺术创新的意义。比如,他于1926年发表了一篇题为《艺术的新运动》的文章,其中写道:“艺术之与吾人的发生关系,就在它‘能使我们与自然暂时脱离,到达一种绝对的境界,得一刹那间的心境的圆满’,否则,吾人固无须乎艺术,艺术亦自失其存在。”“艺术自身的宏力缘何而生呢?邓先生(邓以蜇)很明白地告诉我们是‘......组织的完好,形式的独到’,邓先生所谓‘绝对的境界’,也就是这‘完好’‘独到’的存在。”“邓先生所谓‘组织的完好’,‘形式的独到’,实在就是我们实地作画的人应走的路,你只要对于组织形式有了异常的心得,还怕没有伟大的作品。”[7]
在另一篇发表于1927年的《严沧浪的艺术论》中,刘开渠更为具体地分析了艺术的内容与关系问题:“因为没有认识艺术的‘材’与‘趣’,所以大家会以外表(技巧、题材)为艺术,或以‘理’(人生)为艺术,沧浪看清了这偏激都不是艺术,所以他把它们相提并论,告诉我们艺术离不了‘书’与‘理’。但‘书’与‘理’直接却不能算艺术,艺术使这种‘书’与‘理’经过吾人的心熔铸的,这种结果才是真的艺术。”“于是所谓‘象牙之塔’与‘十字街头’的争执也可以解决了。赤裸裸的‘十字街头’上的人生不是艺术,净玩外面(技巧、题材......)空无内容的‘象牙之塔’里的东西也不是真的艺术。它们要似恋爱的一对男女,有形的、无形的都密密地合起来,彼此浸淫到成了一体,才能产生新的生命—健全、伟大的艺术。”[8]此外还在《徐枋的画》一文中分析说:“不管动或静的艺术,最要紧的是在创造,是在开发从来未曾有的境界;使吾人受一种新的刺激,借以完满在现实界求得的精神生活。这种创造,这种开发,在内的是作家强有力的生命力,在外的是作家独有的作风。所谓‘创作’就是这两种东西的织成。自己的生命,唯有自己的技巧才能充足地,无遗漏地,极为自由地表出。也唯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作风才能容纳自己的生命,所以一个作家固须有强有力的生命力,容纳这种生命的个人特有的作风—颜色,线条,形式,调子—也是非有不可的。否则不会产生伟大的作品。”[9]
由上述文字可以了解,刘开渠已经对如何进行创作有了更为具体的认识,而且他在这个阶段对自己一贯主张的创新也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在发表于1926年的《石涛的画论》一文中,刘开渠表示了对于在作品中以“自我表现”实现创新的赞同,他写道:“‘自我表现’在其(林风眠)艺术上立得住脚,我觉得不管如何表现(方法的),只要能充分地显露自己在作品里边就算对了。因为要作品处处‘著我’,它外在的形式,组织,运笔,设色,自然是各人各异,不会雷同的。这不同,就是创造!艺术能到人人创造,也就够了。所以改良,沟通等,都无须乎劳神费时地去讲。你能充分地表现自己,显露自己在作品内,就算达到了你研究艺术的目的。外面的伎俩问题何必去管它呢。”“如其自己有文人之思想,文人之趣味,又能独创方法,以表现自己,如石涛者,那自是专门以技巧为能事的画匠之流所望尘不及的了。所以我觉得文人画除了具备文人的条件,是要加上‘独自创造,不蹈他人蹊径’,才算顶有价值。”[10]
针对同样的问题,刘开渠又从画家的角度在1927年发表的文章《画家的生命与作风》中写道:“画家的生命与作风能够完全一致,他就是不是大天才家,也不至于制些无力无趣味的东西。如其画家不知道创造与他生命一致的个人作风,只是追慕别人的作风攫取别人的方法,他就是有百分的天赋才能,至多也不过制些华而不实的无动人内心的力量的东西。所以艺术并不是粗粗地简单地能满足我们的视欲就算完事。它要能够震动人心,使人内心有一番新的起动才成。远不过是一个传达者,它的满足与否,适度与否?是没有大关系的。”[11]在评论具体画家的文章里,他也秉持着上述思想。比如刊发于1927年《现代评论》上的《傅山及其艺术》一文,刘开渠在文末总结道:“青主的画第一使我们注意的是,全体不皴擦,不渲染。他用极简单的线条,表现各个形体,联贯各个形体。青主的画第二使我们注意的,是他一往直前,不做作的朴实的表现精神。......青主之所以有这种精神,就在于他对于艺术要表现自我。他之所以能不顾一切的表现自我,在他能超越世俗之生活,而深入一种伟大的生活里。他不好名,不要官,不贪富,他忘掉了世俗一切权利之思,所以他能自由自在的挥写,任情高歌,奔驰于真实的世界!艺术的世界!青主的画第三使我们注意的,是高大宏壮,奇异不凡的邱壑。......青主不搬运人家的邱壑,纯从己意创造新邱壑,来容纳他的人格,再无怪他成功了。”[12]
创新才能使中国的艺术重新具有活力—刘开渠在这一阶段更为坚定地认同这样的观念。他从多种角度、多个层次上去反复探讨何谓创新、如何创新等具体问题,并把自己思考的结果通过理论、评论文章与更多热爱艺术的人进行分享。在新艺术备受关注的时间段内,刘开渠通过比较密集的评论从理论上支持了艺术家的创新行为,汇入到民国时期重要的艺术潮流当中。
三、主张以雕塑表现英雄与人民生活的阶段(留法归国至“文革”结束)
刘开渠留学期间感受了法、意两国经典艺术作品的震撼力,也受到了老师朴舍的影响,反对学院派,主张自由创造,重视天才的发挥。师生二人都推崇一种接近罗丹又比其更接近现实主义的艺术风格。刘开渠在担任朴舍助手期间,经常随老师前往、参加文艺界人士的聚会,增广了见闻,提高了理论修养,更锻炼了思考能力。刘开渠夫人程丽娜后来回忆说:“我逐渐发现他有深厚的文艺理论修养,和他交往得益不少。”
留学生活结束后回到祖国的刘开渠对何谓艺术、何谓艺术家的问题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这种认识在《八八师纪念塔雕刻工作》中论述得比较充分,他写道:“每件艺术品之能存在,是它有一个独异的生命,就是说它包含有一个真理,一个深的人类的情感;真理及毫无虚假的情感是永远不死的,它们的光辉绝不会因人事之变迁而减少,它们感动人心的力量绝不会因日常生活方式之变化而低弱的。”“所谓一件艺术品有生命,而且要有独异的生命者,就是说你这件作品要有一个向来尚未曾经人发现过的东西做内容,你的作品要包含一个新的意境,否则,你的作品不是艺术品,你自然也不是艺术家。”“一个艺术家的天职,一个创造家的天职是在创造新生命,所谓创造者,就是寻求真理,发现人心深处的真感情。这个组织成一件伟大艺术品的真理,真的感情,只有真能竭尽艺术家天职的艺人才能发现,就是说只有毫无其他目的,专为创造而创造的人才能把他们发现。”[13]
刘开渠回国之后的第一件作品被当成了陪葬品,尽管他的内心受到了冲击,但实现雕塑艺术的社会功能与价值的愿望却变得更为坚定。他在创作上更投入、更勤奋,在教学上始终诲人不倦,同时争取各种机会进行宣传,竭力提高大众对于雕塑作品的鉴赏水平,也是为雕塑家营造适合开展工作的社会文化环境。在《八八师纪念塔雕刻工作》里他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一个新的真理,一种新的感情,就是一个新的生命必须有一个新的形式去收藏它,可是新的形式常常是不受社会欢迎的,尤其是当它刚刚出现的时候,所以一个真的艺术家应该为打破世人的旧习惯而奋斗,就是不顾社会的好恶,而继续他的有新生命的创造工作。”“倘使想有伟大的艺术家出现,有伟大的艺术品产生,不但从事艺术工作的人要毫无私心地为艺术而工作,社会上的人们也应该相信艺术家,相信他们的创造力量,让他们有精神上,工作上的绝对自由。”“倘使一个艺术家没有思想上的自由,工作上的自由,他一定做不出伟大的艺术品,好像一个革命家被人夺去了发言及行动的机会,自然革命无从实现了。”[14]
《八八师纪念塔雕刻工作》是在《淞沪抗日纪念碑》(全名《陆军第八十八师淞沪战役阵亡将士纪念塔之雕像》)落成之际面世的,文章内容非常丰富,对于研究刘开渠的思想有重要的价值,对中国雕塑艺术理论建设尤其意义不凡:在详细阐明历史情况的前提下,以比较的方式梳理了中西不同文化环境中纪念碑雕塑的特点,提出了基本普适当时情况的设计思路。现将其论述援引如下:“对于建造纪念物的方法,东西大不相同,中国人立碑,碑上刻字。至于这碑的形式是否与被纪念的人物或事体有关系,是不注意的。碑上的字要写得很好,但这是好在字的本身上,至于字的形式、神气是否能代表被纪念的人物,或事体,没有关系。这完全同我们画个‘二’是记两个的意思一样。这种记号的抽象纪念方法盛行于东方,尤其在中国。西洋人立纪念物,不用记号。他们用具体的方法去把所要纪念的人物或事体表现出来,就是说,他们纪念一件可悲的事体的时候,他们就想出一个可以表现悲的形式去代表。记号式的只有抽象的记事价值,只有对这记号有习惯的人才会了解,他没有艺术的价值,就是说他不能直接对一个观者发生感动力。西洋人的具体表现方法是艺术的,因他是用一个形式,一个体积去直接感动人。我们要纪念一位大人物,一件英武可歌的事体,大约有两个目的:一是纪念人物、事体的本身;一是藉此人物、事体而启发、感化后人。要达到这两种目的,我们的记号式的纪念方法,实在不足。例如中山先生的伟大,绝不是用几个抽象的字可以记出的。这唯有艺术才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人格。唯有艺术的方法,才能使他的伟大的精神永远久地深深地直接地感动现在及将来的,千千万万的民众。圣经、圣书并不能使人人信教,而能打动人心,使人不知不觉,变成了圣徒的,是那些教堂内,表现着圣经、圣书事体的雕刻、绘画。艺术式的纪念物,不但能深深地打动人,并能代表一个时代永久存在,因为纪念物的本身尚具有反映时代生活,包含真理的艺术的价值。艺术式的纪念物也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传记式的;一种是纯粹艺术式的。所谓传记式的,就是完全把被纪念的人物或事体的外形描写出来,至于这些形体是否合乎艺术上的条件,是否有碍于作者的理想之表现,是不管的。这一类的纪念物多半受定做者及同时代的人的欢迎。但这一种很难有充分的艺术价值,它的时间性一旦消失了之后,人看也不愿再看见它了。”“因为作者被事体的形式限制住了,他所感觉到的真情,他所见到的真理不能自那边表现出来。没有真理、真情,就是没有生命的作品,或者可受一时的欢迎,但终不能久存,这个我们在上边已说过。纯粹艺术式的,并非是说,作者完全不顾到所被纪念的人物或事体,不过他所注意的是事体的内容,人物的精神。表现一个战士,他并不一定要一个大炮在战士身边。因为注意内容,不受事体的外形的限制,所以他能自由地运用他的艺术天才,创造有新形式、新生命的艺术品。真正伟大,有价值的纪念物,都是这类纯粹艺术式的纪念物。”[15]
刘开渠对东西方雕塑艺术有着清醒的认识,对什么样的雕塑最适合中国社会的需要也有明确的见解。他将比较抽象的观念与中国的文化现状、革命斗争情况联系起来,明确了以纪念碑雕塑来宣传抗战的思想,也表示了要以雕塑艺术家的身份来投入追求民族解放与自由之斗争的决心。发表于1936年的《雕塑与抗战》中有这样几段话:“雕塑是很重要的艺术之一。艺术是与科学一样,对人类有积极与消极的作用。为了人类能有更高的文化,须注重科学,也须注重艺术。
有了这两种学科的合并进行,才能达到人类幸福之目的。那么提倡科学与艺术,自然不应该忘记了雕塑。”“雕塑能够描写情感,说明思想,寻求真理。雕塑既是有了这样完全的表现方法,那么它自然也是能够如同其他技术一样,可作为抗战建国之宣传的工具。”“雕塑既是可以同其他学科一样的能探寻真情至理,雕塑既是最民众化的,为感化民众最有利的艺术之一,我们就应该十分地注重它,去应用它。”[16]
在形式复杂的斗争环境下,刘开渠始终坚持创作与教学两方面都不放松。他的想法十分单纯而又值得尊敬:只教别人做,自己不常做,岂不是变成了个“说”雕塑的人,而不是做雕塑的人了吗?刘开渠身上的艺术家气质和热情时时能够感染人,在重庆期间,他那一处小小的住所仿佛成都文艺界的“沙龙”。画家吴作人、傅抱石、秦宣夫、关山月、黎雄才等人常常过访;音乐家马思聪等人不时光顾;作家萧军、端木蕻良,诗人曹葆华、牧野、沙汀、何其芳、赵其文等人也乐于盘桓其间。抗战胜利之后,刘开渠前往上海,同进步文化人士曾庶凡、戏剧家陈白尘以及胡风和夫人梅志等人共同度过了解放前夕最黑暗的日子。这样的交往和经历使刘开渠更坚定了走现实主义道路的想法,也把表现人民大众和民主精神当成了自己的使命。他在创作中坚持这样的原则,也不断宣扬这样的艺术思想。他在发表于1947年的文章《中国雕刻的过去与未来》结尾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就历史上看,美术所借用的题材愈广,美术品的内容愈有大众精神与感情,其发展的途径也愈宽而远,其内在的生命也愈充实而有力。新的创作必须紧依着新的题材与新的内容才能冲破前人的作风而创造出来。这个新的题材就是民众生活,这个新的内容就是民主精神。在这个基础上,就是中国雕刻未来的光明途径。”[17]
此外,在《中国美术的生路—兼谈陆地的木刻》一文中,刘开渠明确表示:“现实主义或新写实主义是中国美术的出路。只有完全变成人民大众的一员并彻底了解生活,才能深刻地把握住现实,写实才能正确有力而不歪曲与虚伪。”“要美术新生,第一先须打倒模拟主义、出奇思想与铲除资产阶级压迫。摆脱这个最坏的恶毒的唯一方法,就是紧握着现实渗入、溶化自己在人民大众生活之中。现实生活,群众的心性,不仅告诉你以种种的新形式,而且启示以最丰富、最正确的内容与理想。没有多数人了解的形式,没有正确的思想的美术品,绝不能是好的作品。”[18]
现代雕塑艺术在中国走过了一段历程以后,刘开渠作为亲历者和研究者之一,对多年的创作成就进行了总结,也对中国的雕塑应当如何提高与发展提出了中肯的建议。1959年发表的《雕塑创作的新气象》便是此类论著的典型代表,文章较为全面地总结了新中国建立前10年的现代雕塑艺术创作成就;而文章《提高雕塑艺术的质量》则从思想和实际操作两方面讨论如何提高雕塑艺术的质量这一问题。[19]《雕塑艺术和美—美术家刘开渠谈雕塑艺术》一文则从“雕塑艺术”“什么样的雕塑品才是美的”“雕塑品的创作及其风格”和“雕塑家的修养”四个方面来具体分析何谓雕塑之美以及怎样获得雕塑之美。在“雕塑品的创作及其风格”一节中,他更是提出了雕塑创作需要遵循的原则和应当避免的问题。[20]
对于早年就倍加关注的“艺术需要创新”等观念,刘开渠留法归国以后为之找到了与社会和大众贴合更为紧密的表达方式。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创作为止,刘开渠以雕塑表现英雄思想的能量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释放,此后便没有继续流连于这类题材;而他关注现实,以现实主义手法展现大众生活的热情始终没有熄灭,在不同的时期相继发表了探讨这类问题的多篇文章。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岁月里,与中法文化界进步人士的交流对刘开渠思想的发展有所影响;及至新中国的成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具有纲领性、方针性的文件对其理论思考亦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概括起来,刘开渠的艺术思想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50年代末,有一条清晰的脉络,即表现英雄以鼓舞人民;而从他留法一直贯穿到70年代末的另外一条线索则是表现人民以歌颂生活、创造美。随着时代的进步,中国社会整体的文化主题发生了转变,刘开渠将雕塑艺术与大众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思考方向没有变,在其七十岁高龄以后,他的艺术理论思想又迎来了又一个重要阶段。
四、倡导发展城市雕塑阶段(改革开放之后)
1979年的《体育报》发表了刘开渠的文章《体育与雕塑》,从谈论古希腊雕塑中的体育、人体之美开始,强调了体育题材雕塑作品的重要性。与后来发表的文章系统起来看,能够发现《体育与雕塑》是刘开渠大力倡导发展城市雕塑的一个话语铺垫。此文有一段话表明了刘开渠倡导发展体育雕塑的目的,其中提到了在公共场所普及雕塑的问题:“从古希腊到我们今天,都证明体育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体质增强,提高体态美,是如何的重要;人们的健康身体,美好的体态,对历代雕塑艺术水平,又起着多么大的影响。我希望雕塑家们能为广大群众创作更多更好的体育题材的雕塑品。让体育的美、雕塑品的美,更多地走进我们的公共场所,让它们充满美的气氛,更深地感染广大群众,更快地增强人们的体质,更好地培养社会爱美的风尚。这对于我们完成社会主义事业是有好处的。”[21]
在抗战时期,刘开渠即呼吁让雕塑走进公共空间,但那时主要是试图以此鼓舞和激励人民的斗志。在《八八师纪念塔雕刻工作》一文中,他已经提出了要让雕刻与其所在建筑相协调的观点:“要一个在建筑上的雕刻能伟大,不但雕刻的本体要好,而建筑部分尤其要与雕刻十分调合。我们晓得一个建筑物(建筑、雕刻合成)之能否雄壮,不在高度之大小,而在它本身上的各部式样及各部所合成的整个形势,是否有伟大的精神。它之能否使观者格外觉其伟大,尤在它是否能与它所在的这环境相调合。在外国,每当立建筑物,人们先向艺术家所要求知道的,是以上所举的几件事的设计。至于艺术上的表现工作,艺术家是完全自由的。倘纪念物的建筑部分不能与雕刻部分调合、相称,任你的雕刻如何好,亦将被破坏。”[22]
度过“文革”困难时期之后,刘开渠再次提出在公共场所摆放雕塑,则是为了以美来装点人民生活,并使大众通过欣赏体育雕塑来产生锻炼的愿望,其最终目的是要达到增强全民体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目标。这是与刘开渠本人的思想发展相契合的,他在“文革”中痛失亲人,创作也一度中断,自己又日益年迈,此时的刘开渠对健康和美的渴望格外深切。这也是与时代主题合拍的,当中国即将迎来一个城市化发展的加速期,从各个角度探讨如何建设城市都是值得关注的话题。刘开渠于1981年发表了《谈谈北京市城市规划问题》,文章提出对于城市“要当艺术品来认真设计......要美化又要富于文化性......要保持优秀传统又要大胆创新”[23]。《第一次全国城市雕塑规划学术会议开幕词》(1983年9月)具体谈到了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当时要准备抓好几件大事;《第二次全国城市雕塑规划会议闭幕词》(1984年5月)又相应地进行了一些总结。在这段时期,刘开渠不顾年事已高,毅然前往多地进行讲学、为数个建设项目担当顾问,为发展中国的城市雕塑事业和新时期的艺术发展做出了不可抹杀的贡献。
在致力于推动中国城市雕塑艺术发展的过程中,刘开渠仍然没有中断对专业雕塑艺术教育和雕塑美育普及工作的关注。1980年4月,刘开渠在《文艺研究》上发表《对雕塑创作的几点意见》,再谈一般人物雕刻的创作问题。同年的9月27日,《北京日报》刊发了他的《雕塑艺术欣赏》一文,文章写道:“只有用雕塑艺术的规律和特点去欣赏,才能认识雕塑艺术的、感到雕塑品的美和丰富的意境。雕塑是立体的,要从各个角度去看,要在各种不同的光线照耀下去看。每个侧面,每一光照的变化,都构成一个意境,一幅画面,可供欣赏。其次,题材及灵感是创作的起点,它决定作品的形式和艺术处理。但最主要的是作者所要集中表现的思想、感情。为了突出主题,作者对于自然形象要有所夸张、有所精简和概括,以加强形式感。因为欣赏雕塑品,是从作品的形式上感到和体会到作品的意境的......每个观者对作品各有自己的不同感受,所以,只要观者觉得这件作品感动了自己,使他能够在思想上得到启示,在美上得到感受,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么,这件作品就算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了。”[24]
众所周知,在刘开渠实践自己艺术思想的历程中,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坐标点,即中国美术馆。作为中国美术馆的首任馆长,刘开渠对其建设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在他的主持和领导下,中国美术馆的职能不断健全,展览、收藏、研究、宣传和出版等工作逐步走上正轨。他还牵头策划召开了全国部分省市美术馆专业工作会议,并当选为中华美术馆学会筹委会主任。可以说,他的多重身份和多方面的艺术成就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奉献了不小的力量。1981年《文艺报》刊发了他的文章《美术创作与精神文明》,将创作与欣赏统一到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并提出了三项原则:“一、普及美术品,供群众欣赏,提高精神文明。二、美术形式、风格要百花齐放。三、坚持原则,解放思想,大胆创作。”[25]
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春天里,刘开渠尚在思索如何为现代雕塑艺术开辟新路。时至今日,城市雕塑仍然是颇受关注的议题。发展中的中国几乎每一年都在面对城市建设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公共空间中的艺术要以何种面目迎接观众,要以何种身份在城市中扮演一个恰当的文化角色,是刘开渠等老一辈雕塑人留给当下乃至未来的开放性艺术命题,也是我辈后学需要为之继续探求的命题。
(责编:耿晶)
注释:
[1]刘开渠《艺术上的批评》,刊于《晨报》副刊,1924年7月24日。
[2]刘开渠《禁止展览裸体画》,刊于《晨报》副刊,1924年8月4日。
[3]刘开渠《现在的国画》,刊于《晨报》副刊,1925年5月22日。
[4]刘开渠《敦煌石室的壁画》,刊于《晨报》副刊,1925年6月9日。
[5]刘开渠《评画与看画》,刊于《晨报》副刊,1927年5月25日。
[6]刘开渠《翟大坤的作风》,载《现代评论》,1927年第6卷,第136期,转引自《刘开渠美术论文集》,山东美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32—33页。
[7]刘开渠《艺术的新运动》,载《现代评论》,1926年第4卷,第89期。
[8]刘开渠《严沧浪的艺术论》,刊于《晨报》副刊,1927年2月24日。
[9]刘开渠《徐枋的画》,载《现代评论》,1927年第5卷,第120期。
[10]刘开渠《石涛的画论》,载《现代评论》,1926年第4卷,第89期。
[11]刘开渠《画家的生命与作风》,刊于《晨报》副刊,1927年4月21日。
[12]刘开渠《傅山及其艺术》,载《现代评论》,1927年第6卷,第146期。
[13]刘开渠《八八师纪念塔雕刻工作》,载《神车》第3卷第2期,艺术运动社编辑,艺专消费社发行,1935年3月15日出版,第8页。
[14]刘开渠《八八师纪念塔雕刻工作》,载《神车》第3卷第2期,艺术运动社编辑,艺专消费社发行,1935年3月15日出版,第9—10页。
[15]刘开渠《八八师纪念塔雕刻工作》,载《神车》第3卷第2期,艺术运动社编辑,艺专消费社发行,1935年3月15日出版,第12—13页。
[16]刘开渠《雕塑与抗战》,载《抗战与艺术》,1936年第1期,转引自《刘开渠美术论文集》,第52页。
[17]刘开渠《中国雕刻的过去与未来》,刊于《文潮》,1947年1月第2卷第3期。
[18]刘开渠《中国美术的生路—兼谈陆地的木刻》,载《刘开渠美术论文集》,第59—60页。
[19]刘开渠《雕塑创作的新气象》,刊于《美术》,1959年第10期;《提高雕塑艺术的质量》刊于《美术》,1959年第11期。
[20]《雕塑艺术和美—美术家刘开渠谈雕塑艺术》,载《刘开渠美术论文集》,第103—111页。
[21]刘开渠《体育与雕塑》,刊于《体育报》,1979年10月22日。
[22]刘开渠《八八师纪念塔雕刻工作》,载《神车》第3卷第2期,艺术运动社编辑,艺专消费社发行,1935年3月15日出版,第14页。
[23]刘开渠《谈谈北京市城市规划问题》,刊于《光明日报》,1981年2月22日。
[24]刘开渠《雕塑艺术欣赏》,刊于《北京日报》,1980年9月27日,转引自《刘开渠美术论文集》,第123—124页。
[25]刘开渠《美术创作与精神文明》,刊于《文艺报》,1981年第5期,转引自《刘开渠美术论文集》,第127—129页。